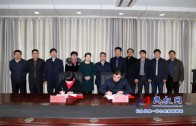杨伟成:站好自己的岗位、为社会留点印迹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宽麟早年留学美国,是我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师,从1920年起的三十年间在天津、北京、沈阳、上海、无锡、南京和华东众多城市都曾因完成很多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结构设计而成为著名的建筑结构设计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教育家,从1932年至1952年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工学院主任、教务委员会主任,直至1952年教育部主持的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后来他被北京市设计院(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身)聘为总工程师。
我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仅在遗传基因方面我亦偏爱数理化与工科,而且在待人处事和设计理念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作为父亲,他对子女们采取轻松式教育,只重身教,不言教。所以子女们在成长岁月中都过得很快活。父母亲给予了我们一个温馨的家。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他的爱国精神,在学生及工程界下属中竭力传授节约材料、资源、节约人力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为人方面与人为善,抵制作假、欺骗、虚伪、溜须拍马等等丑恶行径。他酷爱他的得意学生们,却完全不懂的理财,也不储蓄。他做人的格言是“少说多做”,而且回避政治。他的很多人生哲学理念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们子女们。
由于他与母亲结婚时已经34岁,生我时他已经36岁,因而希望我能早点出道。在此思想指导下。1938年我11岁小学毕业,13岁初中毕业(跳了一级),15岁高中毕业,18岁大学毕业。后者是因为在抗战期间,圣约翰大学领导认为学生们暑假的三个月中什么也干不了,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索性利用这3个月,将一个学期的课程浓缩进去形成一年间由两个学期变为三个学期。由此原来四年学制中八个学期不变,但只需要不到三年便完成了。
我步出大学时正值1945年抗战结束。次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自费留学生考试,如考试及格就可以办理出国护照。当时我和5个同班同学参加了自费出国考试,全及格了。1947年8月六人同船前去美国上学。
我们原来都是土木系的,到美国既可继续读土木系硕士生,也可以转系。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给我建议,说国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已经有很多人才,而暖气、卫生和空调工程师还是很缺人。所以我和另二位同学选择转为机械工程系,插班大学三年级。
美国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其实是个“大杂烩”,专业课程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水力学、内燃机原理、蒸汽热力站、冶金学等,基本上属于专业基础课。至于更深一些的理论,则放在研究生阶段或实习阶段解决。这种理念和前苏联的大学中的教学大纲有很大区别。前苏联的大学据说是设“暖气通风”专业的。
我个人对暖通这个专业和室内给排水专业有兴趣,因为它比结构专业“显形”。结构专业涉及安全问题,在实际设计中需有个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难以从建成的外表显现出有多大安全系数。而设备专业(暖通、给排水)则不同,一旦投入使用后便显现设计的正确与否,有趣也便于总结提高。
我在美国留学四年,前两年从国民政府购得“官价外汇”,1949年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时国民政府已垮台了。我到纽约找了个实习的设计事务所,晚上到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1951年获硕士学位。
我的回国有个“因祸得福”的过程。当年在中国留学生中,明显的可见有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一派倾向于国民党,另一派倾向于共产党。我对“国民党派”的“官二代”和少爷小姐们看不上眼,1948年参加了亲共产党组织的夏令营。我听到他们介绍的解放区状况等,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这一年还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原著,给我十分清新的感觉。1949年到纽约后,有机会遇到更多进步中国同学,参加更多联谊活动。其实这些都是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普通联谊活动,和美国当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和移民局当局在1950年起在麦卡锡反动议员鼓吹的“反共风波”下开始把刚解放的新中国列入“敌对国家”中,继而对有“亲共嫌疑”的中国留学生施加压力。他们的手法一是乘申请签证延期之机传訉中国留学生,甚至加以拘留;二是给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等活动制造障碍甚至下禁令;三是勒令限期离境。
1950年末我收到移民局的传訉,虽然问不出个所以然,但还是有联邦调查局的武装人员来我住处进行搜查,并且随后由移民局来函勒令我在1951年6月下旬离境。好在此时学业刚结束,我也不必逗留了。
殊不知, 我的离境是“ 因祸得福”,因为美国政府政策多变。其政府中的一派人认为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居留美国对美国不利,应该驱逐。另一派人却认为这些中国留学生如果学的是理工医农等专业,回到中国等于帮了共产党,反而对美国不利,因而应该扣住,不让离境。前一派人当政时我被驱出美国,而三个月后的九月份另一派人当政了,便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了。我的五个同船同学结果全被扣下,成为“被难民”。
回想我在美国的四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获得了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其次,我也开阔了眼界,不仅亲眼目睹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和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亲身体会到表面上标榜“ 自由”“民主”的背后还有一副蛮横霸道的面孔。美国的种族歧视尽管不能放到桌面上来, 但还是相当严重的。
我为“因祸得福”而感到庆幸。假如当年的我被禁止离境而滞留他乡,被迫当个“二等公民”,我一定会十分沮丧。